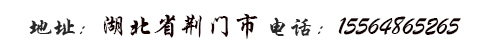依依东望是人心
|
若干年后的清晨,天寒地冻,北风凌冽,司马懿来到渭水河畔,将豢养多年的乌龟“心猿意马”放生。司马懿两鬓斑白,面容憔悴,面对宁静辽阔的天地,感叹道:依依东望是人心。 作为经历了曹魏四朝的元老级人物,司马懿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他这一生都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都在人心鬼蜮中挣扎。他能忍、能干、能输,还能识时务明大体,又能当机立断,心狠手辣。所以他熬过了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一次次身临险境,又一次次化险为夷。他看过太多勾心斗角,太多雄心壮志,太多提心吊胆,太多呕心沥血。这次他终于放走了自己的心猿意马。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年轻时的司马懿深知人间疾苦,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他满足于冬葵汤的人间至味。追随曹丕时,他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只想在保全一家之性命的同时不负中郎将。他看到无数英烈在这乱世战争中化进了泥土里,清明雨下,新坟旧冢葬头七。那时的他不涉军事,不掌兵权,只想着五谷丰登,让百姓有饭吃就是他最大的理想。 人心盼太平,将军盼功名,司马懿简单了。他施行的新政虽然在短期内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但也触及了宗亲贵族的利益。同样是追求安定幸福,百姓们追求的是丰衣足食,宗亲将军们追求的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这一切都需要功名来换。于是,战争成了必需品,所有百姓都要为之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不知何时,司马懿打起了兵权的主意。一为自保,不让将军们乱箭射死,二为名利,为大魏建功立业。他的军事天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除了孔明之外,平生少遇敌手。于是他借刀杀人,借诸葛之手杀死了曹真、张郃,自己独揽军政大权,而后屡立军功。魏明帝曹叡临死时对司马懿说:朕最忌惮的人和最得力的人都是你。驭人无数的曹叡对司马懿也是又敬又怕。 有人说司马家是典型的儿子生老子。司马懿察觉到司马昭有逆反之心,曾在渭水让司马昭发誓永为魏臣。可他非但没能纠正司马昭之心,自己也逐渐黑化,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他虽善忍,但毕竟不是大肚弥陀,也有一忍再忍终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像压弹簧一样,压得越久越用力,反弹的后力就越大。司马家忍得太久,这次爆发时也是气势汹汹。征辽东杀了一万人,灭曹爽夷七族杀了七千人,处决王凌夷三族又杀了三千人。司马家的无坚不摧,催生了血流成河和人心惶惶。老年司马懿视人命如草芥,这究竟是他的本性,还是饱经沧桑后的异化? 我更倾向于后者。没有谁一出生就是罪人恶人,之所以会犯下滔天大罪,乃是时局和环境造就,偶然中有必然。从当年淳朴天真的赤子之心,到如今凶残麻木的权臣心计,人心的蜕变以超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路径而蜿蜒进行,积少成多,积重难返。回溯野心的成长史,就如同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恶心过程循环播放。世事无常,人心鬼蜮,谁敢谈圆满? 某些历史正统派一直强调司马家是乱臣贼子,是千古罪人,身上的污点和血迹是洗不干净的。于是骂《虎啸龙吟》这部剧在美化司马懿,是在给司马家洗白等。我不喜欢研究历史,也不懂什么正统或不正,所以只能从个人角度来评价这部剧——是一部“历史之外,情理之中”的良心剧。有网民说:对待历史,棒子是死不要脸,倭寇是死不承认,我们是死无对证。想来感慨万千。 人心的变化自在情理之中。幼年的童心、少年的良心、青年的野心、中年的小心、老年的唯心、晚年的慈心,都是生命最寻常的历程。阅历增长和环境变迁都会导致心境的变迁。所以不被环境浸染是不可能的,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向生活低头,不然何来成长? 只是人可以选择性浸染。有原则的人像弹珠,尽管在不同的染缸中被染成不同的颜色,但始终是圆润剔透的造型,他的初心不会变。而没有原则的人像橡皮泥,既被染得乱七八糟的,也被扭曲摔打成各种奇形怪状。无人搭理时就像一坨屎,搁哪儿都碍事。 司马懿大概也没想到,他做了一辈子别人的手中刀,但当他成为执刀人时,竟比以往的所有人还要残忍。他所坚守的本心不在了,身边的亲人朋友都离他而去,他的儿子沉迷权谋越陷越深,他自己也尸居余气,苟活度日。“无毒不丈夫”的名言背后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内心挣扎。身处乱世,何来无辜?人心不宁,何来太平? 突然想起胡彦斌《葬英雄》的歌词:这三尺黄土够不够埋你一世骂名,生死约定真爱难寻,是多情是无情拿命来证明,人会变情难尽谎言很公平。以此歌献给《虎啸龙吟》中的司马懿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ongkuiguoa.com/dkgjg/1670.html
- 上一篇文章: 分娩分娩前的饮食原则
- 下一篇文章: 执业药师考试复习之中药学常用歌诀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