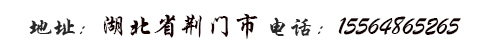东坡食记5目不识书
|
有个成语叫目不识书指读书很少或没读过书。不甚识字或不识字。宋·司马光《涑sù水记闻》卷十六:“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我曾经在襄樊见到过一位当地很有名唱坠子的老艺人,也是目不识书,但却可以现场抓哏出口成章,很是令人佩服。这个成语有个同义词,目不知书,指不会读书写文章。出自《旧唐书·哀帝纪》:“楷目不知书,手仅能执笔,其文罗衮作也。” 一比之下,我是货真价实的目不识书,读书太少,写到古人轶事阅读原文的时候,典故多有不明之处,需要临时抱佛脚到处查证,一篇文章找资料的时间就会花上大半天。古文当中不认识的字儿,念不准的字儿太多,稍不留神就做了白字先生。文章里但凡是标注过拼音的,不是为了让阅读的朋友看的明白,是怕我自己读错了,前面的涑sù水就是个好例子。不怕您笑话,打开字典随便一翻就能找到我不认识的字儿,有些字儿看着眼熟就是念不准。 前文说到的黄雀鲊,应该读成zhǎ或者zhà,我却一直想当然的认为读zuo,幸亏网络发达能很简单的就找到生字读音,要不这乐子可就大了。虽说打开始写公号,我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翼翼,没想到百密一疏还是平地栽了跟头,披绵黄雀漫多脂当中的绵字,我数次读成了锦,这要是台里节目我工资就扣光了。念成锦字实在不该,原句的意思就是说黄雀背后的脂肪很厚,像绵一样柔软可爱,我读成锦是下意识里认为此句是说黄雀背后的羽毛如同蜀锦一样美丽,想当然的自我脑补了,请大家原谅。 现在到湖北黄冈的黄州一带,能尝到一种名菜,和苏东坡是大有关联,名为东坡春鸠脍。这个脍万万不可念成会。《说文》的解释是:脍,细切肉也。这个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出自《论语·乡党》里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再有就是成语脍炙人口,意指生鱼片和烤肉人人都爱吃。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被众人所称赞。首先用脍炙人口来形容文章是五代的王定保,《唐摭言·载应不捷声价日振》:“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皆脍炙人口。” ■珠颈斑鸠,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常见的一种斑鸠。东坡春鸠脍的主要食材。 东坡春鸠脍的起源在四川,《东坡集》里说:“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春鸠脍,就是斑鸠肉炒芹菜。东坡谪居黄州期间,在城东开荒种地贴补家用,一日天寒大雪,苏东坡无意中发现,菜地里冒出了一些嫩绿可爱的小菜,一寸多长气味清新,和他家乡眉州的芹菜很像,这新长出来的芹菜,就是蕲菜。说起蕲菜可是大有来历的。 黄州紧挨着的一个州是罗州,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蕲本意是香草,后来变成了芹菜的专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蕲春县,汉置。以水限多蕲菜为名。”蕲菜,《辞海》释着冬葵。《本草纲目》中亦说,“楚有蕲州,……地多产芹,故(蕲)字从芹。”所以这个蕲菜就是指产自蕲州的芹菜,李时珍认为蕲菜就是古诗当中的葵,“芹,其性冷谓如葵,故《尔雅》谓之葵。”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云梦之芹。云梦就是已经消失的古代湿地云梦泽。依照这个记载,战国年间蕲菜就已经闻名天下了。据说蕲菜兼具水芹旱芹的优点,叶片大而翠绿,作菜脆嫩清馨爽口宜人,清炒或搭配肉食都能相得益彰。 中国人食芹的历史可算是悠久了,芹菜可做汤可入馅料,也可以腌制咸菜,我们甘肃的浆水,就是热面汤浇入芹菜叶中发酵制成。唐代的魏征喜欢吃醋芹,有人说就是腌制的蕲菜。唐代世人杜甫提到过一种用芹菜制作的碧涧羹,语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之二:“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在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卷上有制作方法:“荻芹取根,赤芹取叶与茎,俱可食。二月三月作羹时采之。洗浄,入汤焯过,取出,以苦酒研芝蔴,入盐少许,与茴香渍之,可作葅。惟瀹而羹之者,既清而馨,犹碧涧然。” 东坡见到蕲菜尝试着制作家乡名菜春鸠脍。还特意把这件事儿写成了诗记录下来。《东坡八首》中写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苏家人都喜欢这道菜,写过咏果子狸和黄雀的苏辙吃了之后有大发感慨写下一首诗,“家人旋贴钗头胜,园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来怕春晚,春来会似出云山”。 斑鸠个头不大,初春之时,用鲜嫩的蕲菜一起炒着吃,味道肯定诱人。不过当初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有个疑问,斑鸠大小不过鹌鹑,全身没有二两肉,下油锅炸了连骨头都炸酥了吃着过瘾。不去骨头和刚冒出头的芹菜炒吃,边吃边吐骨头太煞风景了,完全没有了春天的新意。看看这道菜的做法之后才明白,我还是土包子。 选用初春斑鸠胸脯肉,拍松切丝,下绍酒、精盐腌制,以湿淀粉、鸡蛋清拌匀。芹菜洗净切成丝。锅内下猪油烧至五成热,放入鸠肉炒至乳白色时出锅备用。下芹菜丝炒散,发出香味时放入鸠肉,加姜末、白糖、胡椒粉、葱花、滑炒两分钟,起锅盛盘即成。都是好材料炒出来能不好吃吗,话说回来,吃这一道菜,多少斑鸠要遭殃啊。只有胸脯肉,剩下的斑鸠肉又该怎么处理呢?要是换成鸡胸脯行不行呢? 黄州地处大别山西部,各种野味司空见惯,果子狸黄雀斑鸠想吃什么都有,真是羡慕死我们了。冬季雪后,天光放晴,也是进山猎捕山鸡的好时节,苏东坡必然不会放过这唾手可得的山珍。还写了《食雉》一诗,雄雉曳修尾,惊飞向日斜。空中纷格斗,彩羽落如花。百钱得一双,新味时所佳。烹煎杂鸡鹜,爪距漫槎牙。 一百文钱一对儿,价格极端亲民,虽说东坡先生在黄州的时候手头拮据,每日里全家的花费定额在一百五十文钱,可看到有猎户肩扛猎叉挑着山雉来卖,还是忍不住数出一百文买来喜滋滋的带回家,拔毛洗净切成块,小火慢煎熟了吃定然是嫩脆酥松、颊齿留香。或者配上冬笋片,下锅熬汤,出锅的时候别忘了放上些雪底芹菜,山野珍品的特有醇厚,不用放任何调料都是鲜美无比,一家人雪天冬夜围炉夜话,时不时喝上一口热腾腾的野鸡汤,还有比这更暖心的事儿嘛? 别看东坡先生在黄州的日子过的有滋有味,但到了惠州就不行了。公元年,宋哲宗八年十月,苏东坡被贬居惠州,虽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有人说苏轼这首诗是写给政敌们的,意思是你们费尽心思,把我贬到瘴气弥漫的岭南,巴不得我赶紧死在这儿,想多了吧,大胡子我的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天天有新鲜荔枝吃,你们想吃吃不着,怪我咯! 可说了半天,荔枝再好吃也不能当肉解馋,没有肉吃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但东坡先生可是惯于苦中作乐的,没有大块的肉不怕,我自有妙法解馋,伙计,来一锅羊蝎子。 《与子由尺牍谈食羊脊骨》惠州市肆寥落,然每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间亦有微肉,熟煑熟漉,若不熟,则泡水不除,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得微肉于牙綮间,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堂庖所食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 有人用最后一句来做篇名就叫《众狗不悦》。此文写得风趣诙谐,不能不用现代文翻译一遍。子由啊,惠州这地方挺穷的,市场不怎么兴旺,每天就杀一只羊。我也不敢跟当地的各位老大争买羊肉。就跟杀羊的说给我留点羊蝎子。羊蝎子的骨头间还是有点肉的,弄回来之后要把煮熟酱好,趁热剔出来,不趁热剔,就不好弄下来了。然后涂抹上点酒,稍微加点盐,烤到微微有点焦的时候吃。一整天在骨头缝中一点一点地剔着肉吃,咂摸着滋味像是吃螃蟹腿。三五天吃一会,有营养味道好,还挺补的。老弟你吃了三年公款大餐,肉多到咬一口都到不了骨头。怎么能体会我这羊蝎子的美味!所以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秘方,不是拿你开心,真得很好吃的,你要不也试下?不过羊蝎子的肉都给我啃光了,惠州那些等着吃肉骨头的狗就有些不开心了。 原本还想再说说东坡先生在海南时吃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时间不允许了,明天再讲吧,最后附上一首东坡先生的定风波,这阙词是他在惠州时所写,为何他能在逆境中尚可开怀大笑,一切的答案都在其中了。 《定风波》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ongkuiguoa.com/dkggq/331.html
- 上一篇文章: 喝一碗,让你这个冬季不再便秘
- 下一篇文章: 利水渗湿温里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