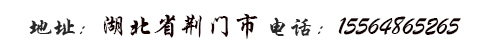讀bull書釋古詩ldquo
|
哪家白癜风医院便宜 https://m-mip.39.net/nk/mipso_7534559.html釋古詩“采葵持作羹”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十二載漢佚名《古詩三首》之二:“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壹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①其中“采葵持作羹”的“羹”字,古今無異文,後人很少表示懷疑,並且往往根據“羹”字去索義。但此詩“歸、誰、累、飛、葵、羹、誰、衣”處在非押韻不可的位置上。上古“歸、誰、累、飛、誰、衣”微部,“葵”脂部②。兩漢時期,脂微二部音值極近,可以互相押韻。羅常培、周祖謨兩先生《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以爲兩漢脂微合流爲脂部③;王力先生《漢語語音史》認爲兩漢脂微仍分開。④但是“羹”先秦至西漢屬陽部,東漢屬耕部。無論是陽部,還是耕部,音值跟脂微二部相差極遠,不可能跟“歸、誰、累、飛、葵、誰、衣”等字一起押韻。時至今日,“羹”也絕無與“歸、誰、累、飛、葵、誰、衣”等字押韻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羹”字必爲訛字。 “羹”是哪個字的訛字呢?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也一直無法解決。直到最近,才有了初步的結論。現在將我思索的過程及結論寫出來,以就教於方家。 一就此詩傳達的信息看,原文的這個字當滿足以下條件:(一)這個字漢代前後必須出現;(二)這個字漢代的韻部必須跟“歸、誰、累、飛、葵、誰、衣”等字相同或相近,能在一起押韻,而且是個平聲字;(三)這個字漢代的字義必須是指能用葵加工而成的一種食物,或伴有葵的一種食物,是窮苦人家的主要食物;(四)這個字字形上應該跟“羹”字相近,能滿足字形訛變的條件。其中,(一)(二)(三)三項都是必要條件;(四)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因爲當一個字處於詩歌的非韻腳字的位置時,人們有可能將這個字換成同義的“羹”,不一定是字形訛變,有可能是寫成同義或義近的異文,或更能傳達出詩歌思想感情的字;但是當它處在韻腳字的位置時,一般來說,除非是字形訛變,否則很難想象人們會有意地將本押韻的字換成一個不押韻的字,而傳承至今。“羹”這個字的前身一定入韻,古今“羹”都不與“歸、誰、累、飛、葵、誰、衣”等字押韻,後人不大可能用“羹”去替換那個本來入韻的字。 根據這些條件,我們可以選擇先秦至中古收字最全的工具書尋找“羹”的原字。《集韻》作爲韻書,收字極全。魯國堯《〈集韻〉——收字最多規模宏大的韻書》:“《集韻》的收字和訓釋首先根據《說文》,但《說文》只收字,重文。而《集韻》收字至字之多,幾達五倍,凡《說文》所無者,則以他書爲據,《集韻》把經史諸子,前代字書、韻書的字盡量搜羅,《集韻》比《廣韻》新增字,‘自宋以前群書之字略見於此矣’(顧廣圻《補刊集韻序》)。”⑤因此,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字,應該能在《集韻》中找到。於是我以《集韻》爲線索,去查找符合上述條件的字,經過排比歸納,竊疑“羹”乃“糜”字之訛,今試證之。 二從音韻上說,東漢的脂微二部變成了中古以下諸韻:脂微皆三韻;中古另有灰咍齊支部分字也來自東漢的脂微二部,戈韻“蓑”等字上古也是微部。爲了滿足上述條件,我們首先應該在《集韻》的這些韻中去找那個沒有發生訛誤的原字。可惜得很,能滿足上述四個條件的字,在《集韻》的這些韻中一個也找不出來。因此,可以推斷,訛成“羹”的那個字,不是漢代脂微二部的字。 這樣,我們得到脂微二部鄰近的韻部中去尋找。據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所列《兩漢詩文韻譜》,脂微二部跟支部押韻甚多,其中支脂微43次,支脂微之4次,支脂微魚2次,支脂錫1次,共計50次。例如佚名《東門行》:歸、悲、衣、啼、糜、糜(“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兒、非、非、遲、歸。這是支脂微合韻,其中“啼、糜、糜、兒”四字是支部字,其它的字分屬脂微二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時期,脂微二部跟支部合韻最多。支部的平聲韻字包括中古佳韻字,支齊兩韻各一部分字。查找分析後發現,滿足上述四個條件的,只有一個“糜”字。 東西漢時期,脂微二部跟歌部也有相當多的合韻。據《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所列《兩漢詩文韻譜》,脂微二部跟歌部合韻的情況是,脂微歌29次,脂支歌1次,脂之歌1次,共計31次,尤以西漢爲多。東漢時期,歌部平聲包括中古歌戈二韻字,麻韻一部分字。查找分析後發現,滿足上述四個條件的,也是一個也找不出。 因此,能同時滿足上述四個條件的字,只有“糜”字。“糜”東漢支部。將“采葵持作羹”的“羹”看作“糜”的訛字,語音上完全能說過去,整個詩可以看作是支脂微合韻。 三從字義上說,“糜”是一種稠粥。“粥”指較稀的粥,“糜”則強調煮得很爛。《禮記?問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孔穎達疏:“糜厚而粥薄。”《左傳?昭公七年》:“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孔穎達疏:“稠者曰糜,淖者曰鬻。”正因爲“糜”煮得很爛,所以發展出“爛”的意思,王逸《九思?傷時》:“憫貞良兮遇害,將夭折兮碎糜。”又“糜爛”連用,《論衡·書虛》:“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 葵,今天又叫冬寒菜。至晚從《詩經》時代始,葵就成為我國古代重要蔬菜之一。《詩?豳風?七月》:“七月亨葵及菽。”《靈樞?五味篇》:“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以葵居五菜之首。《史記》有“園葵”之語,表明葵是西漢種植的蔬菜,《公儀休列傳》:“(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齊民要術》卷三專門介紹了種葵的方法,作出詳細介紹。大約至晚到了明代,葵逐步退出主要蔬菜的行列,今天更少種植。《本草綱目》卷十六《草部》“葵”字下說:“葵菜古人種爲常食,今之種者頗鮮……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李時珍將“葵”由《菜部》移到《草部》。據《中國植物志》第49(2)卷,現在在湖南、四川、江西、貴州、雲南等省仍有栽培冬葵以供蔬食者;北京、甘肅會寧等地也偶見栽培。而“野葵”(即“旅葵”)今在我國各省區,北自吉林、內蒙古,南達四川、雲南,東起沿海,西至新疆、青海,無論平原和山野,均有野生。⑥據我所知,我的家鄉湖北省黃岡市,在我小的時候還種“冬莧菜”,今天仍有種植者。正因爲葵曾是古代重要蔬菜,所以利用“葵”構成了不少詞,例如《爾雅?釋草》中有“菟葵”、“楚葵”、“戎葵”等詞,分別指形狀像葵的幾種草。注意:如今的“向日葵”與古代的“葵”不同,向日葵原產北美洲,大約十七世紀傳入我國;葵菜是我國早已有的品種,它的葉也有向日的特性,所以《淮南子·說林》說:“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張雙棣注:“此葵爲冬葵。”⑦三國魏曹植《求通親親表》說:“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 據古書記載,古人食葵的方法有多種,上引《七月》詩中採用烹煮之法是其中之一。白居易《烹葵》:“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紅粒香復軟,綠英滑且肥。”蘇軾《新城道中》:“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還可以腌制,腌制的葵叫“葵菹”,例如《周禮?天官?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也可以用來幫助其他菜作羹時調味,起到潤滑的作用。例如《儀禮?士虞禮》:“铏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 漢代葵是否能用來煮粥?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古人有時在粥裡放上一些豆子,例如《後漢書?孝獻帝紀》:“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有時加上杏仁,例如《全唐詩》卷一九一韋應物《清明日憶諸弟》:“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古書很早說到“菜粥”,指在粥裏放置蔬菜。菜粥,也就是不另外做菜,連同蔬菜和糧食一同煮成的粥。菜粥是簡陋的主食,其中的菜當然包括五菜之首的葵。《尸子?君治》:“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全唐詩》卷八三三貫休《送僧入五泄》:“五泄江山寺,禪林境最奇。九年吃菜粥,此事少人知。”《全唐詩續補遺》卷二佚名《五言白話詩》之三:“菜粥吃一盔,街頭闊立地。”可見“菜粥”是低級食品,用來填飽肚子。《本草綱目》卷二五《榖部》“粥”下有“葵菜粥”,應該是這種“糜”做法的後代遺留,不過是用在醫療上。今鄂東一帶有“燙飯”,災年常吃,平時也偶爾用來調節胃口,但也是主食。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頁收有“燙飯”:“飯和菜加水煮成的粥。”例證來自湖北武漢、隨州,湖南長沙⑧。另據魯國堯先生見告,鄂東一帶所說的“燙飯”,今江蘇泰州叫“酸粥”。燙飯、酸粥,顯然跟古代菜粥一脈相承。 漢代下層勞動人民沒有糧食吃時,被迫吃糜充饑。漢樂府《東門行》中,男主人公家中一貧如洗,“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他準備鋌而走險,但是他妻子卻勸阻他,“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可見,常年吃糜是窮苦人家充饑的方式。因此,將“采葵持作羹”的“羹”視作“糜”的訛字,不僅在字義上毫無掛礙,而且更符合詩中男主人公的家庭背景。 四從字形上說,根據《集韻》,“鬻”可作“糜”字用,《集韻》忙皮切的“鬻”下說:“通作[麻+下食]”,“[麻+下食]”是“糜”的異體。“鬻”是個訓讀字。它讀zhōu,省作“粥”,今天沿用下來了,所記錄的“粥”是個常見的詞。大徐本《說文》?部:“鬻,?也。从?,米聲。”徐鉉按語:“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俗粥(玉文按:‘俗粥’當作‘鬻’)作粥,音之六切。”⑨小徐本“从?、米”。當以小徐本爲是。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爾雅》‘猶,如麂’之‘猶’,舍人本作‘鬻’,異文同部,是可以定其非形聲矣。”⑩段的意見是對的,“猶”古音余母幽部,“鬻”余母覺部,音值極近。但是舍人本“猶”作“鬻”只能證明舍人本在某一個階段二者音近,不能證明“鬻”原來也是如此。 “鬻(粥)”作“粥”講古代既可讀余六切(《廣韻》),也可以讀之六切(《集韻》)。《儀禮?既夕禮》:“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玄注:“粥,糜也。”《釋文》:“粥,之六反,劉音育。”《禮記?月令》:“(仲秋之月)行糜粥飲食”《釋文》:“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爾雅?釋言》:“鬻,糜也。”郭璞注:“淖糜。”《釋文》:“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云:淖糜也。又與六反。”今天沿用的是之六切。 “鬻”作“粥”講還讀mí,記錄的是“糜”這個詞,專用的字應該是“糜”。《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大徐本引《唐韻》:“靡爲切。”《儀禮?既夕禮》“歠粥”鄭玄注:“粥,糜也。”《釋文》:“糜,亡皮反。”《禮記?月令》:“(仲秋之月)行糜粥飲食”《釋文》:“糜,亡皮反。”《爾雅?釋言》“餬,饘也”郭璞注:“糜也。”《釋文》:“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糜”是稠粥,“鬻”是“糜”的本來寫法,“糜(鬻)、鬻(粥)”是同義詞。由於後代“鬻(粥)”這個詞占了上風,於是有人將它來記錄“鬻(粥)”字,因此“鬻(糜)”就有了“鬻(粥)”字的讀音,成了訓讀字。“鬻(糜)”記錄“鬻(粥)”的用法後來又占上風,“鬻”又有異體“糜”字,於是“糜”專用來記錄稠粥的“鬻(糜)”,“鬻”專用來記錄稀的“鬻(粥)”。 根據《說文》,“鬻”本是“糜”字;後來才訓讀爲“”字,省寫作“粥”字。“鬻”作“粥”講讀mí,已見於中古字書。《宋本玉篇》?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余六切“鬻”下說:“案《說文》‘鬻’本音糜,?也。”《集韻》忙皮切也有:“鬻,《說文》:?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鬻”下注:“《廣韻》云‘《說文》本音糜’者,乃陳彭年輩誤用鉉本也。”根據不足:第一,如果上述三部字書是根據大徐本“鬻”从米聲折合出來的反切,則“鬻”應該歸到脂韻武悲切,不應該放到支韻忙皮切(《集韻》),因爲根據《廣韻》,从“米”聲的字都沒有放到支韻靡爲切下的,而大徐本正是注音“武悲切”。只能認爲三部字書的這些注音不是根據大徐本从“米聲”折合出來的,而是另有所據。第二,作“粥”講的“鬻”,《說文》另有其字。?部:“,鬻也。从,毓聲。”大徐本引《唐韻》:“余六切。”如果“鬻”是“”的異體,《說文》應該將其中一個字形放到另壹一個字形之下,作爲“重文”來處理。但《說文》卻分立爲兩個字頭,“鬻”和“”同屬?部,只隔了三個字,這說明許慎沒有疏忽,只能是他認爲“鬻”和“”是兩個字,不是同一個字的異體。第三,《說文》?部:“,鬻也。”這是拿“鬻”去解釋“”,正好說明“鬻”和“”記錄的是不同的詞,因爲《說文》沒有拿一個字的一個異體去解釋另一個異體的注解方式。前面說過,“余六切”和“之六切”都是“鬻(粥)”這個字的異讀。段氏爲了維護自己“鬻”沒有“糜”這個讀音的見解,又要講清楚“鬻”和“”分立字頭的原因,和拿“鬻”去解釋“”的注解方式,只好在“”下說,“”的反切是余六,“‘鬻’切之六,本分別不同。後人以‘’之切爲‘鬻’之切,而混誤日甚”。他的這個說法沒有可靠的依據。因此,《宋本玉篇》《廣韻》《集韻》認爲“鬻”本是爲“糜”造的古字,是有其根據的,段玉裁之說不能駁倒三部字書的說法。 明白了“鬻”本是“糜”的異體字,“采葵持作鬻”的“鬻”訛作“羹”就好解釋了。“羹”又作“”。“羹”《說文》有幾個異體,?部:“,五味盉羹也。从,从羔。《詩》曰:‘亦有和。’,或省。,或从美,省。羹,小篆,从羔,从美。”列有四個字形,其中正體“”跟“鬻”(即“糜”的早期異體)字形極近,容易相混。此詩中“采葵持作羹”的“羹”原來本作“鬻”,是“糜”的早期異體字;“鬻”跟“”形近,只是其中的“米”和“羔”字形有別,但也有相混的可能性,於是“鬻”訛作“”,再寫作常見字形“羹”。此詩後文接着有“羹飯一時熟”,其中的“羹”原來也應該是“糜”。 五至此我恍然大悟,曹操《苦寒行》:“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跟“烹榖持作飯,采葵持作羹”可能有淵源關係,曹操的這兩句詩應該是點化此詩而來。若然,“持作羹”是“持作糜”之訛,就更增添了一層證據。 如果此詩“羹”是“糜”的訛字,那麽詩中“糜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的內容更具有悲劇色彩。糜是窮人家的主食,菜羹和菜糜不一樣,菜羹是用蔬菜煮的羹,比菜糜高檔,是下飯的菜。因此菜羹不限於底層勞動人民食用,天子和諸侯在一些特定日子也食用,下至士人,食用菜羹的場合更多。《禮記?玉藻》:“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孔穎達疏:“稷食者,食飯也。以稷榖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論語?鄉黨》:“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孟子?萬章上》:“晉平公……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晉平公尊賢士亥唐,在亥唐家裡吃菜羹,可見戰國時家境較貧寒的士人家裡也是經常吃菜羹的。到漢代,士人也有吃菜羹的,《後漢書?崔骃傳》附《崔爰傳》:“爰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古代的菜羹要調以五味,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三“羹臛”引《考聲》:“切肉或菜,調以五味謂之羹。”二而菜糜則是在沒有專門做菜的情況下,連同糧食一起煮,權當下飯菜的一種粥,當然就是更爲低級的食品。 主人公回來時,家中一片淒涼。爲來自窮鄉僻壤的下層士兵,他在軍隊中服役整整六十五年,收獲的只有一年一年歲月的流逝,和一年一年的衰老,無法娶妻生子,贍養父母;甚至一直跟家人天各一方,音訊斷絕,不知家人的存歿情況。在回鄉的路上,還急切地向鄉鄰打聽:“家中有阿誰”;回到家中,家中空無一人,房屋長年無人修繕,殘敗至極,“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榖,井上生旅葵”;田地荒蕪,滴米無存,家貧如洗。原來父母早已過世,墳墓上的土堆得很高,墳旁的松柏已經長成。他孤苦伶仃,只好採摘野生的“葵”和“榖”作飯和糜。 用糜來供養老人,是古代的一種禮制。《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行,賜也。”《後漢書?禮儀志中》:“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這種禮制來自人的生理需要,老人因爲齒牙不堅,消化功能減退,所以宜稠粥。所以《三國志?魏志?曹彰傳》“帝輒優文答報”裴松之注引《魏略》:“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王維《田家》:“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都說出了這個意思。 此詩中,主人公既然“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那麽他離家服兵役時未完婚,歸來時還是光棍漢,只有盡孝的份兒,可是父母雙亡,他煮的稠粥就“不知貽阿誰”了,因此無法給父母雙親盡孝,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傷痛;“出門向東看,淚落沾我衣”,這既寫出了主人公的善良和恪守禮節,也寫出了他的孤苦無依。既然他采採摘的是“旅榖”和“旅葵”,那麽他接下來的生計問題也就突出地顯現出來,嚴重的饑餓也必將伴隨着他。詩歌的主人公此時也八十歲了,他本人也早就到了需要有後人盡孝的年紀,然而他無法奢望有兒女盡孝。這就很典型地從基本人情的角度,揭露了漢代的兵役給貧苦人家帶來的深重災難,從而也烘托了詩歌的悲劇氣氛。 注釋: ①見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年,頁至.標點參考了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年,頁。 ②上古音的歸部採用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商務印書館,年。下同。 ③見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年,頁14。 ④見王力《漢語語音史》,《王力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年,頁81至82. ⑤見魯國堯:《〈集韻〉——收字最多規模宏大的韻書》,載《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年,頁。 ⑥見《中國植物志》,第49(2)卷,科學出版社,年,頁4至5。 ⑦見張雙棣《淮南子校釋》(下),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⑧見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年,頁。 ⑨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影印本,年,頁62。下同。 ⑩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下同。 此採趙振鐸《集韻校本》校勘成果。見趙振鐸《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年,頁69。 見《正續一切經音義》(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關於菜羹的特點,可參黃金貴《說“羹”》,《古代漢語文化詞語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年,頁至。 轉載自《中國典籍與文化》年第1期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孫玉文 編輯:夢軒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ongkuiguoa.com/dkgzzz/4727.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红颜rdquo也可指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