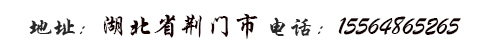大同有个许殿玺
|
编者按:许殿玺其人 近日,浏览百度贴吧之“爱同吧”,偶得许殿玺先生同乡许玮所作的一篇有关许殿玺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吾乡出了个许殿玺”,窃喜。顺着这个题目,又在许玮的博客中找到了全文,从而使我对许殿玺先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也算了却了我多年的愿望。现将原文摘录如下,也让我们这些后辈记住这位在地方志领域做出不朽贡献的许先生。 吾乡出了个许殿玺 许殿玺(~),字文田,大同市南郊区甘河村人,古典诗文研究专家;历任师范教员,大同市教育局干事,口泉区文卫股副股长、文教科科长,口泉中学、西韩岭中学教导处主任,年离职。一生精研古典诗文,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古典诗文的教授、注解、整理、编撰工作中,堪称南郊区当代古典诗文研究第一人。编著有《五代诗选》《古人名地名读音词典》,点校整理《大同府志》《云中郡志》《大同县志》等著作;写作有《姜瓖反叛考略》《云中郡志补正》《阎尔梅等人的大同诗》《南郊区寺庙纪略》等论文。 大约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一堂语文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许殿玺”这个名字。 那天,老师一笔一画地往黑板上写着生字。因为头天晚上大家都预习了功课,所以老师写的那些字,我们并不觉得生疏,但对于意思的理解,还是有些吃不准。写完后,老师逐个领读,课堂上一片朗朗书声。突然,老师停在过道里,捧着书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咱们村有个‘活字典’?”我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对于老师的这个问题,自然无从回答,不知道他说的“活字典”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什么人也说不准。老师见我们摇头,便说,“‘活字典’是咱们村一个很有文化的老人,叫许殿玺。”老师说着,眼睛里闪现着一丝敬佩的神情。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哪懂“文化”这两个字的分量,而且像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叫“许殿玺”的“很有文化的老人”,更不懂“有文化”与“活字典”怎么就连在了一起。 这段记忆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叫“许殿玺”的“很有文化的老人”,不但是我们村的名人,而且在大同市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都赫赫有名,难怪人们称他“活字典”呢。渐渐地,我又听村里人说,这个叫许殿玺的人,三四岁便能背诵《大学》《论语》之类的古代典籍,还说他当年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期间,便在校刊上发表诗文,显示了不凡的才华。我没有见过许殿玺,初听此话,不免惊讶。这么多人对许殿玺既佩又赞,吾辈晚矣,却不知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子竟有这样的“乡间大儒”。 许殿玺、“活字典”,这是作为小学生的我,头一次听说我们村有这样一位让人羡慕的文化人。 我的故乡是晋北很普通的一个村——甘河村(原名德润堡)。许姓家族在村里代代繁衍,人口渐多,成了村中大姓。不知过了多少年,由于各种原因,甘河村的许姓逐渐分成了村东和村西两支。这样的分隔谁也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但许家在甘河村的土地生息繁衍了几百载,同宗同祖。我父亲说,我们属于村东的许,而许殿玺先生属于村西的许,但我们有共同的祖先,都是甘河许姓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光阴流转,这些事、这些因年轮变迁而有些模糊的亲缘关系,我一直想探问个究竟,长大后便不厌其烦地让父亲帮我“捋一捋”,于是再次说到了许殿玺先生。按村人习惯的“辈分论”推算,许殿玺先生称呼我父亲为“叔叔”,虽然我父亲小许先生近四十岁。这么一算,我就该称许先生“哥哥”了。我的语文老师也姓许,比我们跟许殿玺先生的亲缘关系更近,都属于村西的许姓支脉,难怪当初提到“活字典”时,他眼里泛起敬佩的神色。就在捋清我家与许殿玺先生的亲缘关系时,我又听人说,许先生儿时就很聪慧,脑子好使,学习成绩优异,尤其记忆力超常,简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十七岁那年,就读于大同一中的他,统考成绩名列全省第三,被太原的一所学校录取。那是年,乱世里的读书人,哪敢奢望有安稳的光阴潜心诵读诗书,但少年许殿玺,自信满满,憧憬着人生。本打算在省城专心求学,谁料不久日军全面侵华,学校停办,无奈之下许殿玺先生只得返回晋北故乡。求学未果,但这优异的成绩,足以证明他天资聪颖,生而不凡。看来,许殿玺先生是那个年代我们甘河村的“翘楚”。 较之于城市,乡下的读书人很少,书本于农民而言,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在乡村,人们对有文化的人着实羡慕,也着实仰望,但对于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人们很少用“先生”这个词来称呼,至多说一句“肚子里有些墨水”之类的话,或者,干脆就叫“某某秀才”。按着大家的话猜想,许殿玺先生求学的年代,甘河水光潋滟,清澈见底,波光照着一个读书人的身影,悠然来去。四季悄然轮回,读书人的幸福全在纸页和字眼之间,但旧社会求学之路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当初,我听到的所有对许殿玺先生的赞叹之言,说的都是他解放前的经历,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作为读书人的他,显现出的过人天赋。往事重提,对我而言,有些太过遥远。许殿玺先生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读书路,我并不知晓,但心里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脑海里一个诚挚而执著的读书人形象也日渐清晰。人的一生,像是都有注定。年少时的初露锋芒,可能日后会与某项事业结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南郊区赵家小村公社教革委工作,许殿玺先生在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之间有了来往。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父亲得以了解许殿玺先生的人生经历。那时,许先生已经快六十岁了。父亲说,解放前,迫于时局动荡,也迫于生计,许先生除了断断续续念书外,一直在村里教私塾。像早年的家塾老先生发现了他的“天才”一样,他也在朗朗诵读声中,从事着对乡村孩童的古文启蒙教育。正是这些经历和积淀,许先生的古典文学基础日渐扎实,为他日后著述打牢了基础。解放后,许先生当过师范教员,在教育局任职,作过中学的教导处主任。不管在哪个岗位,从没有离开过书本。年离休后,大同市的多所学校相继聘请许殿玺先生讲授古代文学课程。半辈子不离书本的许先生,迎来了生命中最好的做学问的“惬意时光”。父亲回忆说,许先生的踏实、诚朴,以及他做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是有口皆碑的。他写文章,为了一条或几条参考资料和注解,多次坐火车去省城和北京的图书馆寻找第一手资料,因而他选注的《五代诗选》《中国古代爱国诗选》等书中的每一首都精准无误。这是对古人的尊重,更是对后辈负责。父亲简单的讲述,让我更加觉得,我们村有许殿玺先生这样的读书人,真是不简单。因为某某村有一个闻名于十里八乡的文化人,乡亲父老是会引以为骄傲的。 很多年之后,在与父母聊天时我才得知,村中供销社斜对面的一处院落正是许殿玺先生的家。我之前虽不知那院子姓甚名谁,更不曾踏进半步,但供销社一带可是跟伙伴们常去,对那条街还是很熟悉的,竟不知那小院的主人原来正是我们整个村的“活字典”。印象中,那院子不算大,门朝北开,常常是紧闭的样子,院主人一定不喜欢喧闹,不喜欢无谓的应酬,而向往安宁。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应该有的雅致心境。一架书,一方桌,岁月的花开花落全在纸页间呈现。我曾听家人说过这样的话,说是许先生家遇有客人来,如果来者跟他谈的是学问,是读书,他聊三天三夜也兴致不减,若来者只说些家长里短,他会毫不犹豫地失陪,似有拒客于门外之意。这未必是说许先生不好客,而是他觉得时间何其宝贵。文人的精力不应耗损在市井街巷看红火听热闹,而应该在思索中寻求自我的升华。傅山先生《红叶楼》一诗曰:古人学富在三冬;《汉书?东方朔传》言: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我想,这两句用在许殿玺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许先生勤勉钻研,把治学当作立身之根本。时间于他而言,真的就是生命。 我十四岁时,我们全家搬离甘河村到了城里生活。当年的供销社后来已不存,但许殿玺先生家的那座小院依旧。我不知道院里有无树,花草是否长得蓬勃,但我想,离休后的光阴,许先生一定把生命融进了那小院,读书、治学、勘正文献。岁月让一个学问家的后半生匆匆忙忙,但也让他收获了安稳、踏实,还有回望人生时的永不惭愧。按着傅山先生的话,一点一滴的积累,便是一个学问家的“三冬”,是用生命的光阴积攒起来的治学的锲而不舍。父亲跟我讲,许殿玺先生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小车不坏只管推。小车是什么?是身子骨,是血肉之躯,更是一种因爱而生的不放弃。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做到最好,这是多么不容易,这就是成功。心性的煎熬岂止是累垮了身子白了头,更要忍受瞬息万变的世界对肉体和精神的诱惑与干扰。 除了学问让人称赞,许殿玺先生的好人缘也尽人皆知。父亲说,许先生一辈子不跟人红脸,不跟人争名夺利,这是天性使然,是后天的修养,但我以为后天的修养更重要。许先生一辈子做学问,不仅满腹经纶,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腹有诗书而忘记人情世故,没有因为“喝了”一肚子墨水,而变成人们看不起的“秀才”。在我看来,“秀才”这个词多少是含有贬义的,有时暗指某某人光有学问而不懂生活中的一些礼节。我姥爷在世时,常会因身边某人不成器,暗自说上一句带“秀才”字眼的话,以示心里的不满意。许殿玺先生是断不能简单用“秀才”这样的词来形容的。至今在我们村,人们还时不时会提及他的善良,提及他的好人缘和他的知书达礼。对于这一点,我父亲感受最深。许先生比我父亲大将近四十岁,论年龄,其实不必很遵循村里人所谓的“辈分”,但许先生每回见我父亲,都亲切地喊“叔叔”,这让我父亲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学问因为有德行作底,才会更加扎实;德行因为学问的浸润,而更显高贵。许先生的良好家教,深深影响了他的几个子女。时值今日,他们称呼小自己十岁甚至几十岁的本家,都严格遵循着辈分。多年后,我结识了许殿玺先生的两个儿子许端、许正二位先生。他们都是古稀的年纪了,却仍然称呼我一个晚辈“叔叔”,可见许先生当年言传身教对子女们的影响有多深。与此同时,二位先生还对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许先生在世时,逢人问他的孩子:你们父亲做什么工作?许先生总要求孩子们说:是为人民服务!探究许殿玺先生的一生,除了学问吾辈无法企及,还有永远无法企及的一个境界——人格。我们甘河村能有这样的先生,实乃幸事。 时间像河一样,彻夜不息。父辈老了,我长大了,由一个课堂上端坐着听讲的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后来又回到故乡参加工作,对故乡土地走出来的文化人愈加敬畏,也得以了解了许殿玺先生更丰富的一生,以及他治学成果的卓尔不凡。许先生一生参与或单独校点过大量的大同古代文献,其中《大同府志》《云中郡志》《大同县志》三种最为读者熟知。一座古城的历史,详细地收入了三部典籍。岁月磨灭了人的记忆,但文字留住了远去的辉煌。面对卷帙浩繁的三部大作,作为读者的我们,似乎只有感叹,也只有敬畏,可许先生却觉得不足挂齿。对于前两种,他深知其中的瑕疵与遗憾,总觉得如果再下点功夫,可能会更好;对于较满意的《大同县志》,他也从不夸耀,逢人提及,总是说谦逊的话。我见过《大同县志》一书,有时也会查阅。厚厚的典籍,是一个读书人半生心血的凝结。在这样的典籍前,我常常会猜想着作为学问家的许殿玺先生的模样:一身海昌蓝制服,骑一辆老旧自行车,座后面夹着几本书,或许是他编纂的《五代诗选》的书稿,或许是备好的讲义,从甘河河畔骑过来时,老杨树的叶子扇动着春天的风。夕阳坠下去了,余晖涂在红瓦蓝砖的院落间,村庄静谧无声。见他下班回来了,村人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许先生是我们村里最有学问的人,那他在村人眼里便是读书人的参照和权威了。在一个物质生活不怎么充裕的年代,学问,让人变得知足,变得安定。 几年前,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双义和》,我再次让父亲帮着厘清家族脉络。奇怪,我很自然地又想到了许殿玺先生,想到了他之于我们整个村子的意义。小说出版后,有朋友问我,“韩木人”这一形象生活中有原型吗?“韩木人”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整部作品里,他不算是中心人物,但他曾官至清廷,一身清廉,又满肚子学问,总能用他的所学和他的生活经验,解答着人们的困惑,就像一位“智多星”。每当大家遇到难事,或是解不开的心结,总愿意去找他。我在塑造这一人物时,脑子里时时闪现着父亲讲的许殿玺先生的往事。韩木人身上真有许殿玺先生的影子,这一形象,是我对许先生这位本家“大儒”的敬仰与怀念。 许殿玺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的,寿终79岁,那年我15岁,从始至终没有见过他一面,真是遗憾。后来,我见到许先生不少照片,大都是晚年拍的。照片上的他,面容和善、透着乡村文化人的质朴,有一点木讷,有一点“迂夫子”,还有一点小老头儿的可爱。那已经是他七十开外了。从许先生古稀的表情里,我看到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读书人的心境:踏实、严谨、坚韧、坚持。据他的儿子们回忆,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病榻上的许先生,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但依然能熟背《四书》《五经》。人,一世与书不离,何尝不是一种福气。聆听古今圣贤智慧,饱览人世风云变幻,回望曾有的委屈、艰辛与不公,已经不重要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段许殿玺先生的家事。许殿玺先生79岁离世,而他的老伴儿96岁寿终。这个名叫“白大女”的老人,与许殿玺先生相濡一生。他们的婚恋曾有过波折。当年,许先生还在襁褓里,父母便给他与邻村白家订下了“娃娃亲”。旧时代的人,心地纯朴,一个并不算正式的“婚约”,两家却一直谨守。谁料,及至成婚年龄,许先生母亲与父亲先后故去。得知此事后,白家长辈不打算再守约了,担心女儿进了许家门生活无着。然而,白大女父亲觉得既然有约在先,就不能反悔,最终还是把爱女的一生交给了这个读书人。那是年,许先生全省统考摘得“探花”的名声想必也传至白家,或许白家人看到了这年轻后生的与众不同。酒席花轿自然都是女方备下的,白大女略带娇嗔地顶着盖头,嫁给了甘河村的这个读书人。这一守,便是六十年。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一张许先生婚后的“全家福”。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白大女眉眼秀丽,极有教养,一副大家闺秀的姿容;许先生书生意气,聪慧,从面庞可见不一般。跨越一生时光,这段趣事想必没多少人知道,日升月落,光景依旧,这或许就是命定。也就是在听说了这段家事后,我又想起了许殿玺先生的那座小院。我永远记着那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在村里生活那些年,我不曾踏进那小院一步,更不知道院子的主人竟然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一位“先生”。小院溢满了墨香与书香,淡淡的香气飘过,春天的榆叶梅开着季节的声声祝福。那寂静的小院,成就了一个读书人的梦想。春秋更迭,岁月在翻书的间隙滑过,院主人一袭青衫,手捧诗卷,饱读群书,硕果累累,一辈子坚守着文人的品德。还有他的老伴儿白大女,沉默坚贞,相濡一生,这是福,是修为,更是造化。 关于许殿玺先生,时至今日,其实能提到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于他勘正的几部史籍,也不再被人有意摆上书案,更不再热销。当年印数不多的《大同县志》现在并不容易找到了,据说在旧书市场的价格翻了几十倍。书家知道许殿玺先生吗?知道这位一生勤奋钻研古文的老先生吗?或许,翻了几十倍的书价,足见许殿玺先生愈来愈被人认可的价值吧。 世事沧桑,甘河几经变迁,清凌凌的河水永远消失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然而,岁月依旧,故人情浓,等到春来,我愿去村中那座小院凭吊一位“大儒”。花儿开放时,花丛中那个捧着书读的老头儿,一定是许殿玺先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ongkuiguoa.com/dkgjg/10218.html
- 上一篇文章: 再过半个月,柳州将成为全国最美的城市,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