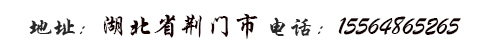华夏意匠城市形状的产生和变迁
|
中国位于亚洲东南部,土地辽阔,历史悠久,建筑遗产极为丰富。数千年来,中国建筑随着社会发展与建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城镇规划、平面布局、建筑类型,艺术处理以及构造、装修、家具、色彩等方面,久已树立一套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理论与缜密完整的营造方法,从而形成东方建筑的一大体系,在世界建筑史中占有灿烂辉煌之一页。《华夏意匠》一书最可贵之处,是在用现代建筑的观点和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问题,并希望能够较为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对中国古典建筑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允鉌先生在此书中尽量引用中外古今有关文献著述以供讨论。 “华夏意匠——经典再读”专题以《华夏意匠》为基础将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提炼整理,带领大家再次感受此书所传达的思想和理念。 城市规划 城市形状的产生和变迁 1 城市形状的产生 中国原始房屋的平面是圆形的,“圆形”是最原始的房屋和群居的布局形式,也有人曾经这样提出,最原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形状也是圆的。理由就是根据甲骨文上一系列表示城市形状的符号都是圆的。例如“邑”字,它的原意是县城,甲骨文上的字形就是上面是一个代表城墙的圆圈,再加上一个人跪在下面。另外一个是“郭”字,意即外城,字形是一个圆圈,上下有两座门楼。这种单纯从字形上而做出的推论似乎未能有很大的说服力,比较确切的说明还是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所表达出来的“聚落布局”。这个聚落布局的总平面形状就是圆的,表示出原始时代一度采取过圆形作为居住区总体布局形式。 甲骨文中的“邑”字(左)和“郭”字(右),“邑”字的构成是一个跪着的人和一个城,“郭”字是一座有门楼的城墙,其中代表城市的“象形”都是用圆图来表示。 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说的:“半坡遗址居住区大体上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里面密集地排列着许多房子。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宽、深各五至六米的防御沟围绕着,沟的北边有公共墓地,东边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如果最初形成的小城市是聚落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由此看来这些城市的平面仍然保留圆形的形式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向心的圆形是最早的表达出“群体”性格的一种意念。再者,“防御沟”和“城墙”的目的性是相同的,在其后的日子,“城”和“沟”都是长期地联同在一起出现。它们在技术上是否曾经分作过两个阶段发展,实在还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在“挖沟”工程上,挖出来的土方堆在沟边的时候,只要稍加整理或有计划地堆放,土堤式的“城墙”就会联同在一起出现;假如要将土方运走,所付出的将会是更大的工作量。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半坡遗址中宽深各五六米的“防御沟”就可以推想原始型的城墙曾经会在此同时出现。也许,这个居住区说不定就是原始型的“圆形的城市”。 西安半坡遗址复原图 图片来源:凤凰网 不过在新石器时代,房屋的平面形状已经演变成为方形了。如果真的十分肯定说圆形就是一种最早的建筑群平面布局以至原始型的城市规划方式未免过于武断。对于“圆形的城市”另一种理解可能就是在构筑城墙的时候,在转角的地方并不采用直角的交角,而是以大圆角来转接,那么在外形上即使是方形或者矩形的城市似乎也成为了圆形。这种城墙的构筑方式不但曾经存在,直至后世还使用得很普遍,尤其是小城,多半如此。不但我们可以在古代的图画中看到这种城墙的形式,今日北京北海的“团城”就是这一类的模式。这一来,以象形而产生的殷代以前的甲骨文,将代表城的符号画成“圆形”实在是真的有它的道理了。 根据《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说法,理想的城市形状是“方”的。有人曾经指出,产生《周礼·冬官考工记》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城市真的如此。反而,此说却对后世的城市规划有了一些影响,“隋大兴”和“元大都”都做出了一个近于正方形的城市,不能说是与此说无关。也许,当时对“方”的理解不只是“方正”,矩形亦属此列。至于城市形状的变化究竟是由圆而方,还是由圆而椭圆而矩形呢,或者根本无此变化过程,这些都是还要研究的问题。 2 城市形状的变化原因 为什么古代的城市大多数是方形或者矩形的“规矩而整齐”的图案呢?不少人解释说这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反映。“城市规划”是“礼制”内容之一,提起“礼”就会和“儒”联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类的巢穴(matrix)由圆而方是一种理性发展的结果,一些人说“方整”的形制主要是由儒家学说的影响而产生,其实在孔丘诞生之前这种形式早就被确认下来。假如,我们从另一方面作一些分析,城市规划之所以取法于“方正”,实在和古代城市必需构筑城墙有关,从几何图形来说,除了圆形之外,最短的周边能包围最大的面积就是方形,其他几何图形或者不规则的图案都会增加周边的长度,换句话说就要多筑城墙。因此,方形或者矩形的城市平面,在建城的工程技术观点来看是经济的,相信,古代的城市计划者或者筑城的工程师在实践中是会清楚这个道理的。而且,早在孔丘诞生之前的商代,城市也大致上是个矩形。 城市规划可以有一种理想的标准的意念,但是,在具体的建城工作上是不可能按照标准化去实施的。因为城市占地广大,问题自比建屋为多;在城址选择上,合乎建城的地理位置不一定具有合乎建城要求的地形,合适的地形又不一定处于良好的地理位置中。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在规划工作上必然要面临如何解决与实际的地形条件相配合的问题。当理想的“方正”的城市设计模式不可能在已确定的城址上铺开的时候,城市就不得不改变成为不规则形状。城市规模扩大后,很多地形条件是不容易实现“方整”的构想的,由于因地制宜的结果,它们就产生了各种的“变形”。明显的例子就是汉长安城,它的南北两边都呈不规则的折线,北城作“北斗”形,南城作“南斗”形,因而称为“斗城”。表面上,城墙之所以作“斗形”,就是基于“体像乎天地”的意匠,事实上,有两个客观因素支配着“斗形”的产生:其一就是北城之外有一条滗河,为了与河流的流向配合,想像出一个“北斗”星座的图案来迁就它;其二就是汉长安城是先建“宫”后筑“城”的,长乐、未央二宫对峙地位于城南,南城修筑时未免不受原有的建筑物的影响 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实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许多城市本来是希望规划成正方形或者矩形的,但是遇到了地形上的问题就缺了角,或者成为了斜线。这就显示出标准的模式受到了“外力”而发生了“变形”,这些“变形”只不过在实际进行建城工作时而得出的一种结果,本身并不是一种预定的城市形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作为核心的“内城”是方的,是最早建立的一个“行政或军事”堡垒,“外城”是根据核心建立起来之后的实际发展情况再行建设,新的城区是自发形成的,发展区分布自然不会平衡,于是新筑的外城便跟着产生不规则的外形。 又如宋代的汴京城,它本来就有一个周回五里的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的内城,再有一个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的“外城”。到了周世宗的时候,在外又加了一道周回四十八里多的“新城”,原来的“外城”——汴州城就变作了“里城”或“旧城”。到宋建都的时候,宋太祖跑到朱雀门楼上,亲自规划了一个从军事防卫观点出发的城墙形式,再行将城墙增筑改造一番(这一故事在上一章“城墙和城楼”一节中已有详述)。这个时候,在方正的内核外就套上了一个不规则的外壳。到了后来,不规则的外形又回复为“方之如矩”,城市的形状和大小就是这样不断地“生长”和“改变”。 宋汴京城 图片来源:网易网 由于市区是会“生长”和“消亡”的,城市的形状就会随着它们的“生长”和“消亡”情况而加以改变。北京城形状的变化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有趣的实例。元大都本来是方形的,但到了明初的时候,它的北部并没有按照预定发展成为“背市”,“市”却在南部城外发展起来,计划中的“商业住宅区”却荒凉一片。为了配合实际的发展,只好将整个城市南移,明中叶的时候,城外南部已成为一片非常繁盛的市区,为了加强城市的防卫设施,便加筑了另一个南城。本来,按照计划是打算全部另筑一个外城的,后因财政困难而终止,仅仅完成南城工程便算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凸”字形的明清北京城。 金中都- 元大都- 明北京城- 明清后的北京城- 8个世纪来北京城的规模和平面形状的变迁。在图中可以看到城市始终是按照矩形的形状进行规划的,形状之所以变化完全是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进行过程中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元大都并不是在金中都的基础上演变,它是一个全新规划的新城,认真算起来,今日的北京城只有7个世纪的历史。在规模上并不是按照日渐增大的规律扩展的,它们会“生长”也会“消亡”。 影响城市“变形”的因素实在是非常多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遭遇或者说“命运”实在是千变万化,并不是规划者所能预料。除了“标准模式”式的变形之外,还有不少城市是一开始就并没有依照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去建城,它本来就是根据实际上的客观条件“成形”。有人说这是古代的城市规划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事实上,任何时候、任何城市都并不会单纯以人的主观愿望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任何违反客观存在需要的形式都不可能成立,更不可能得到发展。“传统”的“方之如矩”的标准城市形制其实也是总结自客观发展规律的“模式”。 至今城墙尚存的中国的一些中小型城市。由图中可见,处于平原地带的多半为规则整齐的正规矩形城市,与地形相配合则形成各种不规则的形状。1.陕西雒南;2.河北束鹿;3.陕西汾州(1.文庙,2.塔,3.泰山庙,4.城隍庙,5.县衙);4.福建汀州(1.县衙,2.司令曇,3.中学校,4.府衙,5.教会,6.府学);5.甘肃平凉(这是古代的一个“带形城市”,今日尚可见其两城并列)。 《水经注》“都野泽”条中有:“凉州城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乃张氏之世居也?。又张骏增筑四城厢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这是很有意思的另一种类型的城市模式,所谓“龙形”,就是不规则的“带形”,也就是现代城市规划中所谓“带形城市”,是交通要道中一种很典型的城市“生长”方式。很明显,这是一种“由内而外”构成的城市,就是说先产生城区后加建城墙。更有趣的是这个带形城市后来发展了它的“卫星城”——“城厢”,并旧城为五而组合成为一个“城市群”。这是一种“分散式”的卫星城市发展方式,是今日城市发展的“流行模式”,不想4世纪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先例。历史上,并不是仅此一例,目前江苏也存有这种“五城”组合为一体式的城镇。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带形城市和组合式的城群,事实上,城市除了依照正统的方式规划外,更多时候是根据客观条件的要求而出现它们自己应有的合理形式。 还有一种就是依自然条件自然形成的城市形状。三国时的吴都建业(今南京)被称为“石头城”。据古籍记载:“石头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自清凉寺北,覆舟山下,江行自北来者,循石头城转入秦淮。”当然,当南京城扩大时,自然而来的城市形状就消失,还是代之以依山背水作势的人工所规划而来的外形。不过,在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石头城式”的自然形状城市是很多的,因为无论任何时代,特殊的地形条件往往都是城市发展难于逾越的规限,城区在特殊地形前停留下来,它们往往就成为了城市的边界,决定了城市的形状。 城市的发展常常会冲破作为城市界线的城墙的规限,新的城市平面形状就追随着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变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带形城市和组合式的城群,事实上,城市除了依照正统的方式规划外,更多时候是根据客观条件的要求而出现它们自己应有的合理形式。 本文内容只用于专业学习及交流 文字内容摘自《华夏意匠》(天津大学出版社,),版权属于天津大学出版社 推荐阅读 华夏意匠——古代的城市和规划 华夏意匠——都城的盛衰和兴亡 “扫“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ongkuiguoa.com/dkgcd/10058.html
- 上一篇文章: 行业聚焦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乡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